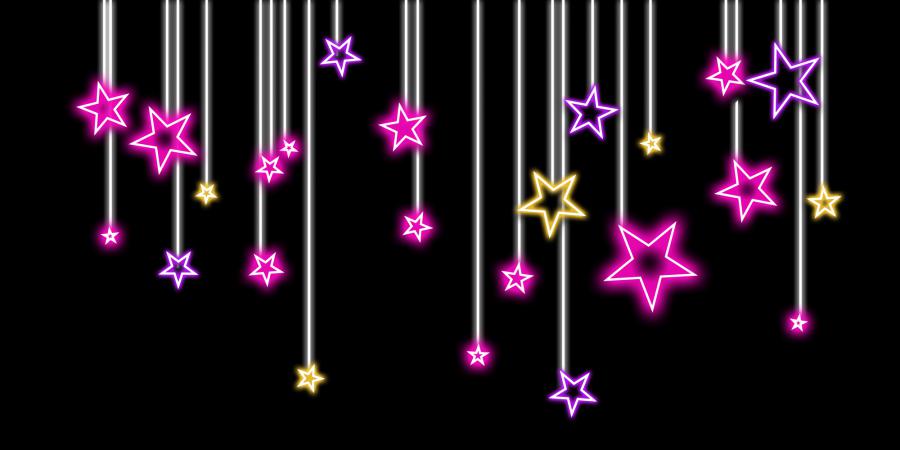
●张良英
匆匆岁月不饶人,不知不觉间,我已迈入80岁的门槛。身体大不如从前,过着那种一本书一杯茶的散淡日子。11月22日,我有幸聆听了马行老师的《中国西部地理与石油文学》讲座。
马老师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诠释了中国西部地理与石油文学的关系。西部地形地貌复杂,而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,必然会在作品中留下西部独特的地理印迹。西部的戈壁、河流、草原等,使石油文学呈现出悲壮、苍凉、雄奇、浩瀚的特点。这让我想起顾伟《云端漫步》里的几句诗:
值得品味的越多/让人依恋的感觉也越久/一字岭,这个延伸了乡愁的分水岭/岭南有隐入群山的巴音沟/准噶尔盆地从岭北一泻千里……
马老师讲得深入浅出,特别是那一句“写文章就是要把每一个文字擦亮。”太经典、太形象了。为把每个字擦亮,他的《塔城东地理记》八易其稿,终于将那首诗“打扮”成自己想要的模样:
我长途跋涉,来到塔城/又从塔城一路向东南行走90公里/——东经83°36’,北纬46°14’/我站在了亚欧大陆中心点
地理测绘数据为证:/此时,整个亚欧大陆之上/我就是距离大海和远方,最远的那个人
游客和行人都走了,留给我的静寂和孤单/似乎比亚欧大陆还要大
马老师对标题也是精益求精,为了文题更加相应,最终将《塔城东地理记》更名为《亚欧大陆中心点行记》。最后几句,他将初稿的“人们”改为“游客和行人”,更加具体可感,末尾句“留给我的静寂和孤单/似乎比亚欧大陆还要大”,文字夸张有力,简直是神来之笔!让人沉浸在无尽的遐想之中,眼前顿时浮现出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的场景。
逐字逐句地打磨,不断地修改,这就叫“推进到极致”。多一字则多余,少一字则不足;分行恰到好处,哪怕是一个标点符号,也要做到各施其责,各尽其位,起到朗朗上口,增强节奏感的效果。
下面我想谈谈马老师的散文《库鲁克塔格山上的星空》:
那个夏天,我和勘探队的一支小分队,就像一小块会移动的戈壁滩,从哈密大南湖戈壁径直向南移行了两个多小时,来到库鲁克塔格山北沿。
文章一开篇,时间、地点、人物就有了。“就像一小块会移动的戈壁滩”,形象的比喻一下子就把文章写活了,引人入胜,起到了让读者欲罢不能的效果。接下来:
夜越深,星星越多。而星星们,不是一颗挨着一颗,而是一群挨着一群,仿佛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集会。
库鲁克塔格山上的白天有多寂寞,晚上的星空就有多繁华。
我和作者一样,看着看着,隐约觉得,这库鲁克塔格山上的星空,也许并不在我们熟悉的这个宇宙之中,有可能存在于另一个平行时空。作者笔下是与别人眼中不一样的库鲁克塔格星空。
我捡起一块石头,举到阳光下端详半天。恍惚觉得,这遍地油亮的石头,应该就是库鲁克塔格山上星星们的家——星星们大致的生活方式是,白天居于这石头之中,等天黑了,就从一块块的石头中走出,然后升到天上,发光发亮。
我给石头们起了名字——“星星石”。
因“天近星辰大,山深世界清。”而引出“星星石”。
两个月后,我把那几块石头带到了万里之外渤海边上的小城,带到了俗世。
那几块“星星石”尤其喜欢窗台那个位置。天一黑,住在里面的星星就会悄悄走出。
读罢上文,我直呼:“妙啊!”作者借库鲁克塔格山的星空和戈壁石抒情,巧妙地变“静”为“动”。
此文结尾更加耐人寻味,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余地:
在渤海边,那些喜欢观星空的人,会发现天上多了几颗星星。只是,他们肯定想不到:那几颗星星,都是我从库鲁克塔格山上带来的。
这是一篇不事雕琢而真情流泻、不假粉饰而心迹坦露,情景交融意境美好的好散文。其实,散文写作,就是一种发现。用自己的眼睛发现这个世界上属于你的一点一滴,以此延伸开,去感动自己,然后感动别人。
|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