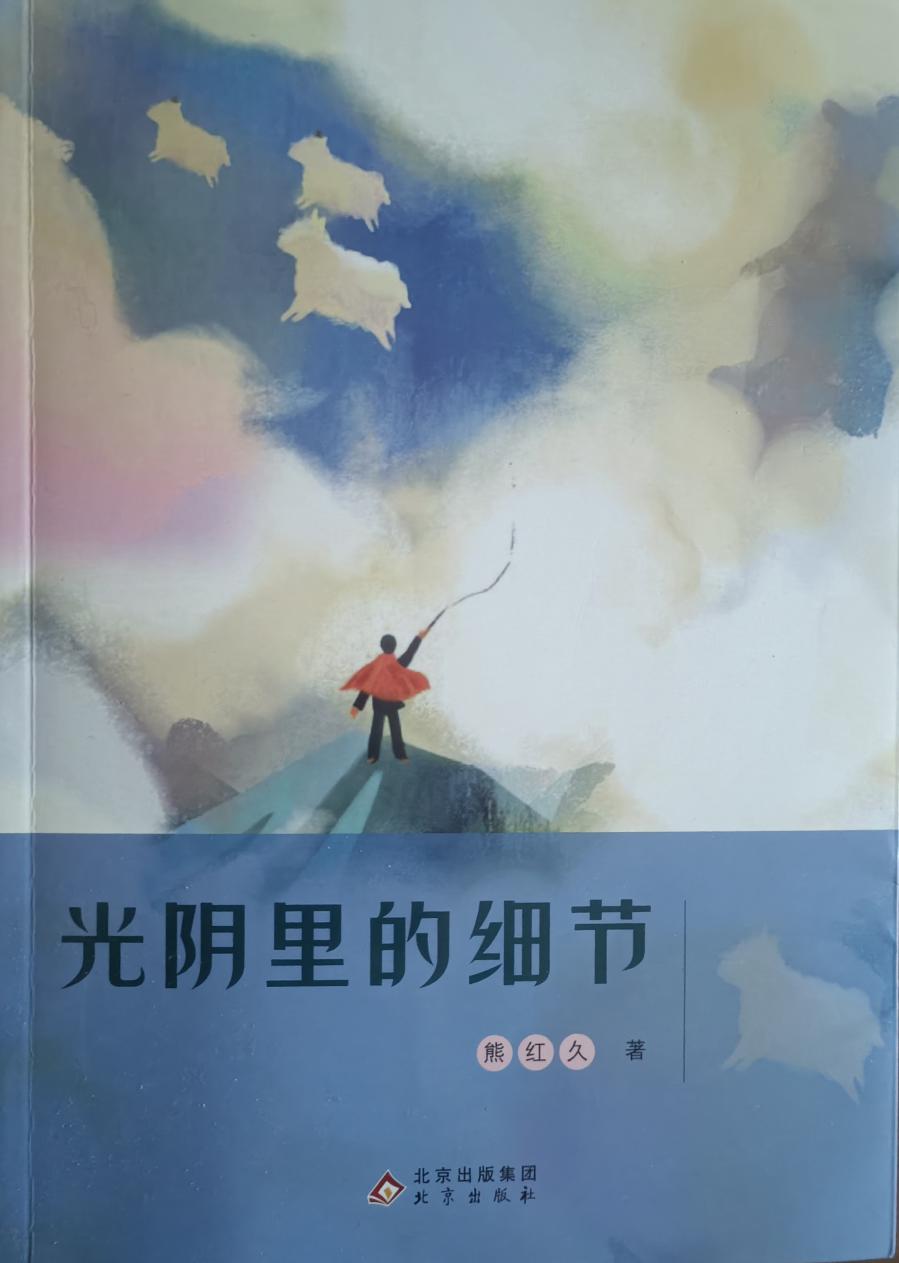
徜徉在熊红久散文的 字里行间 品味 语言之美 ●罗基础 何谓美?《说文解字》定义说:“美,甘也。”甜味一样的快乐感。亚里士多德说:“美是自身就具有价值并能同时给人愉快的东西。”美是一种引起快感的事物。我国现代美学家说:“美是有价值的乐感对象。”“美的本质不过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;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;一个灵魂唤醒另外一个灵魂。”美的事物千差万别,只要有价值即正能量、能够引起观赏者情感愉悦,即称之为美。 我阅读熊红久的散文,就有这种感觉,徘徊在字里行间,犹如徜徉于花丛中,犹如回味一杯美酒,在慢慢欣赏语言之美的同时,细细琢磨语言营造的那种意境,忍不住再看一遍,甚至在内心里默读。 熊红久说:“语言是文章的皮肤。”既然是皮肤,那就得完美,悦己悦人。他还说:“好的语言,既是好文章的基础,又是好文章的载体。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惊叹,翻开一页书,只读了几行,就内心欢喜,仿佛找到了失散多年的挚友,想迫不及待地与之推杯换盏,促膝谈心。甚至感觉每一个字都是自己的亲人,这便是语言的魅力。” 翻阅熊红久的散文,随意采撷几个片段,便能感知其语言魅力。 熊红久散文的语言之美,在于他笔下的大自然被赋予了生命。用人或生物以及肢体语言来描述自然界。如此,读者易与自然产生共情,有一种设身处地的亲临感,在读者眼中,自然景物就有了审美意蕴的艺术意境和意象,从而使大自然的活力与生机得到充分彰显。 徜徉在熊红久的散文里,独山子在线官微,23分钟 描写天山山路的文章很多,但熊红久独辟蹊径,以独特的语言描述山路的崎岖、狭窄和路上汽车的渺小。“当道路细成了大山的一道掌纹,汽车就像甲壳虫,缓慢行走在山脚下。” “匍匐地面的路在山势的托举下,显然想站起来,却又被沉重的车轮,压弯了腰。” “路越走越像一根鱼线,而车子则是一条上钩的鱼,在上下起伏和迂回环绕间,从沟底慢慢提到了水面。这个水面,已经跃居到了海拔两千米高的山脊上。”(《当雄浑的天山打开自己》) 在此,将天山之路的细长和狭窄比喻成一道掌纹、将山路的起伏想象成一个人或一个生物,可以想象出这个“路”心有不甘,想站立起来,“压弯了腰”,说明路的不平。而汽车成了甲壳虫、成了从谷底跃到山脊的鱼。尤其是将路比做钓鱼的线,将汽车比作上钩的鱼,堪称神来之笔。乘着这句生动语言的翅膀,我们飞到山顶,俯瞰那些在盘山道向上爬行的车,确实有“汽车如鱼,路如鱼线”的感觉。 又如麦子和麦田,这是很多诗人、散文家笔下的最爱之一,而把麦田比喻成麦子的母亲,我还是第一次见,读起来感觉很亲切,有温度。“不少倒戈的麦茬和堆放的麦秸,使得这片麦收前看上去整齐划一的土地,显得有些衣冠不整甚至丧魂落魄,就像弄丢了自己孩子的母亲。曾经被它哺育的血脉,已经走远了,或许正走在另一种价值的路上。” (《生命的麦田》) 这里,麦田作为麦子的母亲,望着没有麦子的田野,她是多么沮丧,是不是像丢了孩子的祥林嫂?这样,麦田就有了生命的气息。 再如,拟人词的运用,可以让那些物的东西活起来,让静物有了动感。“一幢幢土屋好似一群累倒的汉子,直挺挺横卧在田边。” (《伙伴》) 在此,那些土屋犹如累倒的汉子躺在田边,可以想象是多么疲惫,而土屋的疲惫说明外形之破旧,没有精神。“车站是一排土房,脱落的墙皮上钉了几个木板站牌。因常年暴晒,木板裂缝,远远望去,站名们咧开嘴打着哈欠。” (《道路之幸》) 站名在张嘴打哈欠,说明这个车站很旧。 同样,拟人词的运用,让动态的景物有了入木三分的体验。“一下车,冬季就证明了自己的存在,手和脖子都被寒风安排进了上衣内,站不稳的声音,无法被耳朵抓住,很快就落在身后了。” (《硬过时间的石头》) 在此,寒风是有思想的,指挥手和脖子躲进了上衣里,寒风呼啸的声音是站不稳的,耳朵抓不住它们。读到此,一种亲身经历的感觉扑面而来,仿佛身临其境。“闷热和汗臭狼狈为奸,覆盖了触觉和嗅觉。”(《道路之幸》) 狼狈为奸这个词比喻互相勾结干坏事,是有生命的。此时作者将闷热和汗臭两个体表感知的、没有生命的词比喻成两个坏人,赋予了生命的特质。此句引发我的联想: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,闷热和汗臭两种东西交织在一起是什么感觉,此时,那种触感和气味倏然涌到眼前。 熊红久散文的语言之美,还在于他使用夸张的想象和比喻,冲击读者的视觉感官。对于读者而言,与文章最先接触的是视觉,是读者通过视觉引发的兴趣,而阅读兴趣来自语言和情节是否吸引眼球。所以,文章是否吸睛,成了读者是否继续阅读的前提。对此,熊红久有一段精辟论述:“文字只有在读者目光里才能存活。所以,留住目光,就是留住文学活着的理由。” 人对于自己的身体有真切认知、感知, 读到与身体相关的词,本能地会产生联想,唤起读者的内心呼应,增强读者的意识流动。 在熊红久笔下,干涸的湖底成了自己的骨头,当站在湖底时,犹如踩在自己的骨头上。脚踩着自己的骨头,那是一种怎样的痛感?一种发自体内的疼痛感觉会猝然袭来。“当一双脚站在干涸的湖底的时候,其实,那种心痛的感觉,就像是踩在了自己的骨头上。”(《湖殇》) 天山高耸入云,当高到一眼看不尽时,他用了另一种语言表达:“第一次去天山大峡谷,你会惊叹于壁立万仞的巍峨,似乎瞳孔已经装不下了山的高耸。(《当雄浑的天山打开自己》)” 读此句,我会想到杜甫的“荡胸生层云,决眦入归鸟。”一个是眼睛里装不下,一个是极力睁大眼睛看,是不是有点儿异曲同工之妙? 说起哮喘,大家都知道,他用哮喘病人来形容发动机,这让我对发动机的声音有了一个参照体,贴切形象。“发动机的声音滞重而混杂,像患有哮喘的重症患者。”(《道路之幸》) 真诚的形体表达是什么?是敞开胸怀。在熊红久笔下,天山峡谷就是天山敞开的胸怀,以这种方式向世人昭告天山的真诚与柔情。“绵延二千多公里的天山,在这里裂开了一道口子,把自己的肺腑向人类摊铺开来。”(《当雄浑的天山打开自己》) 胡杨有三千年之说,他用几个具有生命力的名词和动词来彰显胡杨的坚强不屈:“一些死后的胡杨,仍顽强地站立着,像一只只从沙漠中伸出的遒劲之手,想扼住命运的咽喉。有些訇然倒地,却决不愿被漫漫黄沙轻易掩埋,它们奋力拱出地面,成为不朽的雕像。”(《思想的胡杨》) 在此,他使用“遒劲之手”“扼住”“奋力拱出”几个拟人词,让我感到了胡杨的倔强力度。 正因为我们熟悉自己的身体,当我们的身体与他物有了联系之后,更能让我们产生共鸣:“因为感冒,他嗓子里的百灵,脱了一些毛,但他的表情是没有瑕疵的。”(《夜宿安龙堡》) “我们这些孩子就像被砖窑烧坏的砖头,随意丢在窑外,没人在乎。”(《伙伴》)“我作为主谋,红柳条又一次在臀部写满了象形文字,注解不当行为。”(《暖冬》) 在此,他用嗓子里脱了毛的百灵形容声音有瑕疵、用烧坏的砖头形容不被在意的孩子、用象形文字形容挨打的痕迹,很灵动,很有画面感。 更多冲击我视觉的美妙语言可以信手拈来。 譬如在《湖殇》一文中,他这样比喻枯萎的艾比湖:“我脚下的艾比湖正在丧失这些青春,就像一个散失了光鲜的干瘪水果,躺成一汪奄奄一息的物证。那些越来越多从湖底裸露出来的丑陋的盐碱污泥,总让我联想到一具即将风干的木乃伊,一个湖的木乃伊。” 读到此,我想到蔫苹果,想到木乃伊,这就增强了对艾比湖枯萎的印象。 又如在《夜宿安龙堡》一文中,他这样描述去安龙堡的感受:“仿佛藏得太浅,就会被偷走了似的,安龙堡乡被双柏县藏在了哀牢山的最深处。先用两个小时的山路,颠簸出内心的困惑,再用九十九道弯,摇晃出视线的昏眩。车门用剧烈的声响,向我们预报,这可不是一个很随意就能抵达的地方。” 读到此,我知道,安龙堡是“藏”在深山里的,道路是颠簸加摇晃的,还有车门的预报,它们可以颠出困惑、摇出昏眩、提醒来之不易。这些词句让我有一种身处其中的感觉,不由得想起那些漫长而隐秘的山路,那些远行的人。 再如在《道路之幸》一文中,他这样写道:“阳光像烧红的烙铁伸进车内。贴在窗户上遮光的报纸,毫无用处。”他把阳光的炽热比作烧红的烙铁,想象奇特,感官似乎受到强烈刺激,让我过目不忘。 熊红久散文的语言之美,除了以上表现手法之外,还有作者心灵世界的直抒胸臆式的独语。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:“世上最美的东西,是天上的星光和人心深处的真实。”熊红久作为叙事的参与者,在文章中或多或少留有自己的情感足迹,作为抒情的主体,自然有更多的真实情感表达。由于其真实和直白,就有了强烈的“代入感”,让读者循着作品的足迹向前行走。 在《当雄浑的天山打开自己》一文中,熊红久这样表达自己对天山的情感:“天山是用来仰望的,就像散文是用来抒情的。”“这里的辽阔,配得上你的眺望,这里的高耸,扶得起你的仰叹。”在此,作者以主观情绪表达出对天山的崇敬:对天山,必须敬仰,因为它值得你眺望,能扶起你仰望感叹的头颅。 在《夜宿安龙堡》一文中,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心境:“子夜时分,睡眠丢在了神经之外,只好站在宾馆五楼的阳台,俯视整个小乡。灯光躲进了虫鸣里,虫鸣又被微风抹去,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了。熟悉了光亮的眼睛,不知道该把船桨划向何处。小时候的静谧,用了几十年的时间,竟跑到了这里。” 我循着这段文字的小径思考:时至子夜,睡眠丢了,灯光躲在了虫声里,而虫声又被微风抹掉了,好一个静谧的夜晚,安静得让眼睛无处安放。哦,这不就是小时候的静谧吗?竟然跑到了这里!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意境。 在《湖殇》一文中,他这样表达自己的无奈与情绪:“这其实是一段很残酷的过程,就像目睹着自己重病的亲人,在你面前一点点憔悴、枯萎,而后,死去,却无可奈何。” “时常看到一些赞美艾比湖的文章,对它仅剩的三分之一的水域,进行热情歌颂,听上去就像是赞美一个病入膏肓的人美丽的服饰和迷人的发髻。此时,我就会情不自禁地低下头,想起‘商女不知亡国恨,隔江犹唱后庭花’来。不知道在鱼缸里长大的鱼,会不会朗诵有关海的诗句。” 对于艾比湖的日渐缩小,就像目睹自己亲人的离去,那是怎样的一种伤悲?以目睹亲人的离去来表达他对湖面缩小的无奈,同时对那些为艾比湖的现状唱赞歌的人予以讥讽,说他们好似不知亡国恨的歌女,就像鱼缸的鱼在朗诵海的诗句。 在《生命的麦田》一文中,他这样描述自己与原野的关系:“暮色将我和鸽子对视的距离调和得越来越模糊了,整个田野也像有黑汁在慢慢注入,我存在的标志因为夜色的来临而逐渐被淡化了,使我慢慢洇成了原野的一部分,就像被微风吹起的麦秸秆的草香是阳光的一部分那样,弥漫在天空里无法散去。”这里,作者是原野的一部分,正如麦秸的草香是阳光的一部分一样。读起来意境很美。 在《被一本唐诗护佑》一文中,他这样描述一本旧唐诗与自己:“到了外地,洗漱完毕,临睡前打开包取书阅读,内心霍然被电了一下,目光里躺着一本泛黄的《唐诗选注》。由于时间久远,封面的红墨水的章子已经斑驳淡化了,但这并不影响它一下把我拽到三十年前。”一本旧唐诗,引发了三十年前的回想,而且是一下拽回去的。这个“拽”字,动感十足。 在《我的草原》一文中,他这样描述去草原的心境:“从一个城市,向着草原进发的时候,其实我的心已经开始绿了。”人还未到草原,心就绿了,一个“绿”字了得,让人眼前一亮,不禁拍案叫绝! 在《思想的胡杨》一文中,他这样表述胡杨之美:“胡杨之美,美在孤寂,美在绝望,甚至美在死亡。” “而那些死去的胡杨,用枯槁的手,指向我们的灵魂,以自然的名义,向苍天控诉。” 在这段充满张力的语言中,通过“孤寂”“绝望”“死亡”几个词赞颂胡杨之美,引发我对胡杨三千年之说的联想。而“指向”“控诉”则是一种追问,引发我对保护大自然的思考。 在这些有质感、有激情的词句引导下,我沿着那些有质地的文字发出的光亮,向前行走和思考,因为这里有作者的文学修养、审美情趣和思想境界,值得研读。 熊红久的散文之所以耐读好看,就是因为文字优美、形象生动、嵌入精准,体现了他的价值观、美学追求和艺术涵养。正如他所言:“语言是散文展示的外形与气质。”对语言的锤炼,他有自己的见解,他在《把一篇文章养大成人》中说:“语言最怕走平常路,就像一个人行走闹市,再宽阔的身体,也会淹没在人海之中。独辟蹊径,找到迥异而又恰当的语言风格,彰显独特的个性表达,才是赢得成功的有效法则。” 是的,阅读熊红久的散文之后,我认为他的语言有雕琢之美,有淬炼之功,独树一帜,读之感之悦之。正如一首好诗能找到诗眼一样,他的每篇散文都能看到让我不忍离去的词语,有的让我惊叹:“原来这个词还可以这样用!”有的让我赞叹:“这个比喻真是恰如其分!”有时我会会心一笑,有时会情绪随之起伏,有时会产生联想……在获得美感的同时,增添了一份自然知识、社会知识,从而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。 熊红久的散文之美,包括他的文章构架、立意和主题、内在逻辑、语言节奏、叙事细节等诸多方面,语言只是一方面。同时语言也不会孤芳自赏,它只是整个散文花园的一朵艳丽的花,它与文章的其他部分构成整篇散文的一大片芬芳。正如他所言:“语言不是孤立存在的,语言和内容互为一体。一部作品是字与字、词与词、句与句、段与段的有机整体,它们互相倚靠、互相支持,才最终成就一种独特的气息。” 当下是个匆忙的时代,有些人步履匆匆,甚至灵魂已经跟不上前进的脚步。前行的路上,是那些充满诗意的语言向我招手,让我驻足观赏,熊红久的散文便是其中之一。正是这种语言之美,让我不忍急遽而行。很庆幸,我与这些优美的文字相遇,在这些文字的滋养中体味美感。
|


